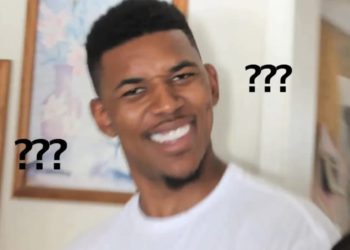霍華・馬克斯認為,迄今為止的關稅發展如同足球迷所稱之為的「烏龍球」,隊員不慎將球送入自家球門而造成對方得分的情況。本文源自橡樹資本發表文章,由霍華・馬克斯,橡樹資本聯席創辦人及聯席董事長本人所撰。
(前情提要: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克斯的最新觀點:你該拋棄幾十年來的舊評估眼光 )
(背景補充:貝萊德CEO投資者信全文:比特幣正蠶食美元儲備地位,代幣化將引領資本革命 )
2008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紐約證券交易所收盤後不久,雷曼兄弟突然申請破產的訊息震驚全球。此前,貝爾斯登和美林相繼申請紓困 / 宣告破產,而緊隨其後,瓦喬維亞銀行、華盛頓互助銀行和美國國際集團也相繼陷入危機。於是市場參與者迅速得出結論:美國金融系統正瀕臨崩盤。
局勢已顯而易見(與數日前截然不同),在以下多重因素的疊加效應之下,金融機構可能或將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塌:
(一)金融放鬆監管;
(二)房地產狂熱浪潮;
(三)非理性的抵押貸款;
(四)將抵押貸款結構化為數千種評級虛高的分級證券;
(五)高槓杆銀行對這些證券的投資,以及
(六)銀行之間高度關聯而引發的「交易對手風險」。恐慌情緒發酵,市場似乎陷入了無止境的螺旋式下跌。
我當時認為,有必要對這些事態的發展及未來的前景略陳己見,於是在四天後釋出了題為《無人知曉》(Nobody Knows)的備忘錄。我一如既往地承認自己對未來一無所知,但在舊有預期被全盤顛覆的情況下,這種一無所知更勝以往。無人知曉這場螺旋式下跌是否會停止,於我而言更是如此。儘管如此,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假設其最終會停止,因此應當在金融資產價格大幅折價之際大舉加倉。
當時無人敢妄稱自己「知曉」未來,包括我在內。我只能通過推斷得出以下結論:
我們無法篤定末日何時降臨,
縱使知曉末日將至,我們也束手無策,
若末日最終並未降臨,為此所作的一切舉措反而會釀成災難,
以及絕大多數時候,末日終究不會降臨。
顯然,上述結論無一建立在知曉未來的基礎之上。但除了將資金投入市場,包括機會七期 B 基金中尚未動用的 100 億美元資金,我看不到更合乎邏輯的選擇。我們設立該基金的初衷,正是為了把握困境債務領域中的重大機遇。而當機遇來臨時,尤其是考慮到我們在困境中能以折價 —— 和驚人的收益率 —— 買入最優質的債務,我們怎能裹足不前?然而必須承認,我們對未來會發生什麼毫無頭緒。
我無法妄言自己能夠分析未來。事實上,我認為「分析未來」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未來尚未發生,並始終受到無數複雜、不可量化、難以預知且不斷變化的因素影響。我們可以思考未來,推測未來,但並無可能分析未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當然也是如此。
2020 年 3 月,我沿用了 2008 年那篇備忘錄的標題,撰寫了《無人知曉(II)》(Nobody Knows II)—— 這是我在新冠疫情期間撰寫的首篇備忘錄。文章引用了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克・利普希奇(Marc Lipsitch)的觀點:人們通常基於以下三點做出決策(一)事實依據,(二)從類似經驗得出的有根據的推論,以及(三)觀點或推測。但鑑於當時既無適用於新冠疫情的事實依據,又無類似的經驗,我們僅剩下推測這一選項。
關於 2008 年危機以及我曾親歷的其他市場動盪 —— 包括當下 —— 我想說的是,我的決策並非穩操勝券,行動時亦難消忐忑。投資領域根本沒有確定性可言,在市場轉折和劇烈波動時期尤為如此。我從未確信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但只要推理出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必須朝著那個方向邁進。
前景未卜
在我 2 月僅供客戶參閱的備忘錄《回顧 2024》(2024 in Review)中,我曾用「不確定性」一詞概括川普政府的特徵。這位總統的決策思維較之歷任更加難以預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未必遵循連貫的意識形態,而且常常會進行戰術性的調整和修正。但值得注意的是,長久以來川普一直抱怨美國在世界貿易中遭受不公待遇,而且至少從 1987 年起,他就一直主張支援徵收關稅。儘管如此,即便我們預見到他會加徵關稅,其政策力度仍遠超預期。顯然,市場也始料未及。
上週的事件讓我們想起了 2008 年發生的事件及其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所有規則均被推翻。過去 80 年形成的世界貿易的運作方式可能就此改寫。其對經濟乃至世界整體格局的影響完全無法預測。我們再次面臨重大決擇,卻依然缺乏事實依據和歷史經驗可供參考。真正的無人知曉 —— 本篇備忘錄的大部分內容都將圍繞那些無法確知的事物展開。但我希望它能幫助您釐清思路、評估事態。
我要指出的是,在當前的局勢下,不存在真正的專家。經濟學家雖有分析工具和理論可用,但在此情境下,任何學者或模型得出的結論都無法讓人確信無疑。現代史上從未爆發過大規模貿易戰;因此,所有理論都未經實踐檢驗。投資者、企業家、學者和政府領袖都會提出建議,但他們未必比普通認知的觀察者更正確。眾人皆知的結論顯而易見,比如物價可能會上漲。真正關鍵的隱微真相反而難以洞見。
我堅持認為,即便對於通過預測來應對未來的人而言,單有預測仍是不夠的。除了預測本身,還需要權衡其成真的概率,畢竟並非所有預測都具備同等價值。在當前環境下,我們必須承認預測的準確率必然不及往常。
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當前局勢中充斥著大量前所未有的未知變數,而這有可能演變為我們有生之年最重大的經濟變局。這裡不存在所謂的預知性,唯有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而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執意以確定性甚至信心作為採取行動的前提,我們將會陷入無所作為的僵局。或者說,恕我直言,如果我們自以為做出了確定無疑的決策,那麼我們很可能是在犯錯。我們必須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決策。
但同樣需要銘記:決定「不採取行動」並不是「採取行動」的反義詞,其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不採取行動的決定 —— 保持投資組合不變 —— 與做出改變的決定一樣,都應被審慎考量。被恐慌的投資者視為避險之策的諺語 ——「不接飛刀」和「靜待塵埃落定,柳暗花明」本身並不能用來指導我們的行動。我非常喜歡市場分析師沃爾特・迪默(Walter Deemer)一本著作的標題:《買入時機到來之時,你卻望而卻步》(When the Time Comes To Buy, You Won『t Want To)。導致價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不利事態的發展令人恐慌,抑制投資者的買入慾望。但是,當不利事態紛至沓來,通常是果斷出擊的最佳時機。
最後,鑑於川普的戰術思維特性,必須牢記一切皆可瞬息萬變。如果他通過施壓迫使對手讓步後宣佈勝利,這並不足為奇… 又或者,如果他通過升級對抗來回應其他國家的反擊,也在情理之中。因此,週五我在沃頓商學院論壇所言,如果有人認為其知道三個月後的關稅稅率,我敢打賭他肯定錯了 —— 甚至無需知道他預測的具體數值。
關稅
川普總統實施關稅政策的動機何在?其理由是否成立?政策宣佈當日,我聽聞一名電視評論員認為川普的「衝動」確有幾分道理。他的目標是什麼?其包括下列部分或全部內容:
- 提振美國製造業
- 鼓勵出口
- 限制進口
- 縮小或消除貿易逆差
- 通過產業本土化提高供應鏈安全性
- 遏制針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 迫使其他國家坐上談判桌
- 為美國財政部創收
必須承認,每一個目標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可取的,也是關稅政策的合理預期結果。
只可惜,事態沒有想的那麼簡單。問題在於現實世界(尤其是經濟領域)存在二階、三階連鎖反應,這些都必須加以考慮。如果沒有這些影響,經濟學就會像物理科學一樣可靠,就像「如果你做 A,那麼 B 就會發生」。正如理論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所說,「想像一下,如果電子有情感,物理學會變得多麼困難。」
經濟和市場幾乎完全由人構成,而人的確是有感情的,作出的反應不可預測。在經濟學中,其他人將對行為 A 以及行為 A 產生的結果 B 作出反應,我們必須考慮他們的反應會引發什麼後果。影響不僅往往重大,而且難以預測。此外,政治在當前問題中扮演著舉足輕重且難以預測的角色,並遵循著它自己的一套邏輯。
川普的關稅政策可能帶來哪些後果?清單很長,其中許多後果都尤為嚴重:
- 其他國家的反擊
- 物價上漲和通膨擡頭
- 物價上漲與消費者信心下滑導致需求萎縮
- 美國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衰退和失業
- 供應短缺
- 世界秩序發生鉅變
需要關注的線條很多,如果我試圖一一詳述,我們將永遠無法完結本篇備忘錄。我在此簡要論述幾點。
有些國家會進行談判 —— 畢竟,借用川普的術語,在多數情況下美國「手握王牌」—— 但有些國家則不會,可能是因為其決策者展現出強硬姿態,從而導致事態升級。加徵「對等關稅」總體而言不太可能帶來任何積極效果,反而可能使得雙方處境更趨惡化。即便我們將要遭遇的問題比其他國家更為輕微,也沒什麼值得欣慰。
毋庸置疑,關稅將擡高物價。關稅就是對進口商品徵稅,終須有人承擔。這既適用於從國外進口的商品,也適用於在美國製造但包含進口材料或零部件的商品。這意味著其影響將非常廣泛。雖然關稅在口岸由進口商支付,但成本通常會轉嫁給最終的商品買家,也就是消費者。理論上,製造商、出口商、出口國或進口商可以選擇自行消化稅負以維持業務,但他們不會樂意為此削減利潤,況且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承擔這部分成本。
值得回顧的是,我在 2022 年 3 月的備忘錄《國際事務的鐘擺效應》(The Pendulum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指出,在 1995 年至 2020 年期間,美國耐用消費品價格按實際價格計算下降了 40%,總通膨率平均每年僅 1.8%。耐用消費品主要包括汽車、家電和電子產品,其進口占比頗高。試想,如果當時限制或者抑制低價進口商品,通膨又會如何?
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前述三大目標真能實現,促使更多在美銷售的商品轉為本土生產:
第一,在多數情況下,美國並沒有足夠的現成製造產能可以呼叫。例如,我懷疑美國是否有工廠能夠生產電視或電腦液晶屏。要建立能滿足大部分美國需求的產能需要耗費數年時間,意味著在短期內將會出現供應短缺及/或售價很可能維持「原價 + 關稅」的水平。
第二,為恢復製造業職位而新建的工廠需經歷漫長的審批建設週期,其相應的建設成本必須基於對未來多年盈利的預期才能合理化。這進一步增加了決策的複雜性,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已經給決策帶來了挑戰。試問哪位 CEO 會僅因這些可能面臨重新談判(或由下屆政府廢除)的關稅政策來承諾投資?不要忘了,川普在其首屆任期簽訂了《美墨加協定》並於 2020 年開始生效,以取代於 1994 年開始實施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現在又以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取代《美墨加協定》。
第三,美國的技術工人數量可能不足以完全替代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當前為我們生產產品的工人。
第四,最初美國人為什麼購買進口商品?因為更便宜。美國為何流失就業職位?因為同樣的工作,美國工人薪資更高,但產品品質卻不足以支撐更高售價。這正是美國的大眾汽車進口量從 1950 年的 330 輛激增至 2012 年的 40 萬輛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美國的關稅太低。很簡單的真相就是,外國商品的成本通常低於美國本土製造的同類商品。即便未來關稅高到讓「美國製造」的產品比「進口商品 + 關稅」的成本更低,其絕對價格仍將高於一週前(也就是徵稅前)的價格。無論如何,美國本土產品的售價幾乎註定高於美國民眾所習慣購買的進口商品。
由於大多數美國民眾支付必需品後收入所剩無幾,物價上漲可能導致生活水平下降。除非工資與物價同步上漲,但這種情況一般不太可能出現,否則我們將面臨危險的通膨螺旋。
物價上漲很可能導致銷量下滑,進而擠壓利潤率。我最喜歡的經濟學家(這說法本身就像個矛盾修辭,就像我從不預測經濟走勢)——Brean Capital 的康拉德・德奎德羅斯(Conrad DeQuadros)認為,企業利潤率是預測經濟衰退的最佳領先指標。當利潤率承壓時,企業會停止新的投資,並採取裁員和其他成本削減措施,而這往往會引發經濟下跌。
經濟學本質上是關於選擇的科學,充滿權衡取捨。這一點在貿易和關稅領域尤其如此。例如,最近大量報導聲稱(真實性待考),2018 年對進口鋼材加徵關稅,為美國鋼鐵行業保住了 1,000 個就業職位。但美國使用鋼材的行業流失了 75,000 個職位(或未僱傭潛在的新員工)。要如何做出這些抉擇?同樣,正如我在 2016 年 5 月的備忘錄《經濟現實》(Economic Reality)中所寫:
一邊是因中國產品而喪失製造業相關工作的 320 萬美國人的利益,另一邊是成千上萬不得不為進口產品支付更高價格的美國人的利益,該如何權衡?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在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人們的不安情緒越強烈,其承擔風險的意願就越低。在我們可能面臨的這個不確定性的世界裡,人們可能會猶豫不決、不願達成協議,並且可能會為每單位的潛在利潤支付更低的對價。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將經濟活動描述為由「動物精神」驅動,他將其描述為「一種自發的行動衝動,而非無所作為,也並非量化收益乘以量化概率的加權平均結果」(根據維基百科)。這種衝動通常源於樂觀情緒,或許正如消費者信心所反應的那樣。那麼,在未來的環境中,積極的「動物精神」的來源又將是什麼?
國際視角
關稅政策的影響遠不止於經濟層面,更深刻波及國際局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貿易對全世界產生了巨大的有益影響。隨著戰後重建開支、技術和管理進步、基礎設施改善和資本市場擴張,加上全球化經濟浪潮,共同造就了「水漲船高」的經濟繁榮。誠然,各國和人民的受益程度確有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是獲益的。我認為這正是過去 80 年總體和平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如此,我們有幸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時期之中。
全球化的主要益處被稱為「比較優勢」。每個國家都有相對擅長和 / 或成本更低的生產領域,與其他國家形成某種互補關係。如果每個國家專注生產優勢產品進行出口同時向其他國家購買自己不擅長的其他產品,由此開展國際貿易,通過提升整體效率實現集體福利最大化。正如我週五在 Bloomberg TV 所說,「義大利生產意面,瑞士專精鐘錶,這讓我們所有人都獲益」。但如果由於貿易壁壘,義大利必須自己生產鐘錶,瑞士必須自己生產意面,兩國民眾可能最終會需要以更貴的價格購買以前習慣購買的進口產品,或是購買品質較次的本國產品,又或兩種情況可能同時出現。
大多數商品在其他國家的生產成本更低,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工資更低,這一事實令美國民眾尤其受益。雖然代價是流失數百萬就業職位,但讓全體美國人事實上獲得了遠勝於僅能購買本土商品的生活水平。這正是沃爾瑪非食品類商品大多為進口的簡單原因。
再引證一個幫助構建了更好的世界的因素,我將美國在後二戰時期的行為描述為「源於開明的利己主義,對世界其他國家表現慷慨。」根據馬歇爾計劃,我們贈予(而非借予)西歐數十億美元的重建資金。同樣,1945 年至 1952 年期間,麥克阿瑟將軍見證了日本的重建和經濟振興。自那以後,美國(一)提供了大量海外援助,(二)大力投資發展中國家醫療體系,(三)推動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留學教育交流,以及(四)向全球輸出正面形象。這些舉措無不彰顯慷慨本色。在每一項「交易」中,我們的付出都超過直接所得,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譏諷我們是「冤大頭」。
沒錯,這堪稱慷慨施予,但正如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述:馬歇爾計劃「為美國商品開闢市場,培育可靠貿易伙伴,並助力西歐建立穩定民主政體」。這是相當不錯的回報。他國人士獲得大量無償援助,但這些計劃毫無疑問對美國亦有助益,包括限制競爭對手意識形態擴張,使其他國家與美國結成防禦同盟,以及助力美國成為全世界最繁榮的國家。我不希望看到美國變成孤立主義者。
但是:這個過程很有可能被我們逆轉。
我們可以與我們的貿易伙伴相互對抗,讓我們的盟友感到受霸凌和勒索。
我們可以迫使曾經依靠我們獲取資本和其他形式援助的國家轉向中國和俄羅斯尋求支援。
我們可以讓其他國家感覺必須減少在美國的投資,以及減持美國國債。
前兩點可能讓我們失去重要盟友,削弱各國對民主制度的好感。正如我朋友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所說:「你無法一邊樹敵一邊施加影響。」而第三點可能對美國財政狀況產生巨大影響。
迄今為止,全世界對美國經濟、法治和財政穩健的高度評價讓我們贏得了「信用金卡」地位,信用額度沒有上限,也不會有催款帳單。這讓我們能夠在過去 25 年間每年以財政赤字執行,過去 45 年也只有四年例外,包括在過去五年間每年新增上兆美元的赤字。換言之,我們一直能夠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維持生計 —— 聯邦政府的開支援續超過其稅收和行政收費收入。這已導致美國出現最糟糕的情況:36 兆美元國債,以及由此造成的聯邦政府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我並不指望聯邦政府會突然負責任地行事並平衡財政預算,因此我不禁疑惑我們還能依賴這張信用金卡多久。
其他國家購買美國國債的意願會降低嗎?他們會認定我們的財政管理不再可靠嗎?
即便我們維持全球最強信用,他們會出於擔憂、不滿或政治動機而減少購買嗎?
如果國債拍賣失敗會發生什麼?(我料想美國聯準會會購買未售出的證券,但我對美國聯準會通過給銀行貸記存款產生資金來購買國債感到不安。最終,資金從哪裡來?)
如果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認可度降低,我們還會維持全球最強信用嗎?
如果國債的買家要求更高的利率,赤字(以及國家債務)情況又將如何?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一些貿易赤字可能已經被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如果這種情況停止,美國國債的利率會發生什麼變化?
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更久遠時期,美國一直「手中有牌」。川普相信美國的實力以及利用實力變現的能力。這就是他在關稅問題上的舉措:不再為世界其他國家「買單」。不再進行能夠產生長期利益的慷慨解囊,而是進行索取公允價值的交易。
我收到了很多關於週五在 Bloomberg TV 上露面的善意回應,我想用一位觀眾的評論,就此話題得出結論: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川普的貿易和製造業顧問] 等人認為,日本在汽車領域領先美國對美國的未來造成了威脅。
日本確實在此領域取得了領先,並始終保持這一優勢。
但自那以後,美國經濟規模相比日本已擴大一倍有餘。即便考慮人口變遷和貨幣升值,增長也已翻倍。儘管在汽車領域失去領先地位,美國經濟規模仍然翻了一倍,或者經濟翻倍是否應部分歸功於失去領先地位?電腦軟體和飛機發動機的利潤率遠比大眾市場汽車的利潤率高得多。(粗體為筆者所加)
日本利用其生產汽車的優勢,而美國轉向其可以獲得自身優勢的其他商品。這不正是充滿活力的全球經濟應有的運轉方式嗎?
正如我在 9 月份的備忘錄中所提出的,政府試圖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努力使其經濟 —— 如若不受干預可沿自然軌道運轉 —— 迎合政策偏好,這種做法是否明智?關稅是一種「外部因素」或「人為因素」,其目的是:(一)抑制本可以實現的出口,從而(二)幫助國內企業實現如果任由其自行運作就不會實現的銷售。代價是什麼,又由誰來承擔?
結論
在我看來,迄今為止的關稅發展如同足球迷所稱之為的「烏龍球」—— 隊員不慎將球送入自家球門而造成對方得分的情況。這種情況與英國脫歐非常相似,而我們已經知道其結果如何。英國脫歐讓英國人民在 GDP、士氣和同盟方面付出沉重代價。對政府聲譽和穩定性造成了損害。而這一切皆是其自釀的苦果。
我喜歡我這一生中事務以往的執行方式,恰好跨越了我所討論的 99% 的戰後時期。我們的部分政府開支顯然曾被濫用,有在國內的、亦有在國外的,我們的國家債務亦非值得慶賀之事。但我很享受在一個和平、繁榮和日益健康的世界中生活,我並不希望看到這種生活發生轉變。僅僅數月之前,美國經濟表現良好,前景樂觀,股市創下歷史新高,到處都在談論美國例外論。如今,如果川普關稅政策生效,美國經濟可能比任何其他情況下都更快地陷入衰退,更高通膨和大範圍經濟錯位。即使關稅完全取消,其他國家也不太可能忽視這一事件,並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無需擔心與美國的關係。
不可否認,關稅政策或許能實現部分前文列出的目標。美國製造業可能增長,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和更可靠的供應鏈。我們在世界貿易中的待遇可能變得更加公平。財政部的收入也可能增加。
另一方面,某些預想的利益可能遙不可及。特別是在減少貿易逆差方面,只要美國更強大、更繁榮並因此擁有更強的購買力,美國從其他國家購買的商品不太可能比其從美國購買的少。美國的工人薪資待遇更好,意味著美國製造商品的成本不太可能低於國外生產的商品。
期望的結果可能會實現,負面的影響也可能成為現實,或兩者兼而有之。然而,必須牢記的是,任何收益可能都需歷經數年調整方能顯現,而代價卻大概率近在咫尺。
金融市場又會如何?過去幾天,經濟展望已發生巨大轉變,股市因此大幅下跌。一如既往,核心問題在於市場當下反應是否恰當:是恰到好處、過度,還是不足?這個問題甚至比以往更難回答,因為幾乎沒有人相信,未來的經濟世界不會與我們迄今為止所生活的世界有顯著不同,甚至可能更糟。一方面,如果宣佈的關稅維持不變,並且他國的反擊措施導致全面貿易戰,經濟後果可能非常嚴重。但另一方面,冷靜的決策(以及政治上和股市上強勁的撥亂反正)如能夠佔據上風,可使得關稅回落至損害更輕的水平,甚至可能為自由貿易帶來增益。
美國聯準會可能如何應對?衰退風險可能催生更激進的降息舉措以刺激經濟。或者通膨的威脅可能導致原本計劃的降息被推遲。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與更典型的需求驅動型通膨相比,提高利率等對抗通膨的措施,在對抗由加徵關稅導致的通膨方面,也許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標題尤為契合美國聯準會的行動:當然無人知曉。
在橡樹所涉足的市場中,對違約的擔憂(並非沒有根據)已導致收益率息差形式的風險補償顯著上升,導致可獲得的信貸收益率出現了顯著的淨增長。與此同時,我們預期困境的發生率將會上升,對訂製化資本解決方案的需求將會有所增加,我們最新的機會型債務基金很可能會加速部署。
借用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名言,歷史總是押著相同的韻腳。因此,正如我為此備忘錄複用我在雷曼兄弟破產後所撰寫備忘錄的標題一樣,在此我還要借用該備忘錄的結語:
18-24-36 個月前人人都在興致勃勃地買入資產,形勢一片明朗,資產價格飆升。如今難以想像的風險近在眼前且已在定價中顯現,探尋以折價買入資產合情合理:昔日珍寶已被投資者棄之若履(那些被連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的嬰兒)。我們正在積極部署。
就我個人而言,我有幸在宣佈關稅當天拜訪了蒙特利爾的投資人,並在次日拜訪了多倫多的投資人。我走訪加拿大的時機真是太巧了!我在每次會談的開場都表示,與數億美國人民一樣,我尊重加拿大,並認為加拿大是美國的夥伴和盟友。反響激動人心。這正是我們所有人與世界各地朋友們聯結的良機。
📍相關報導📍
台股週一難逃跌停!財經專家預測跌幅落在8.5%至10%,PTT股民:下週畢業季